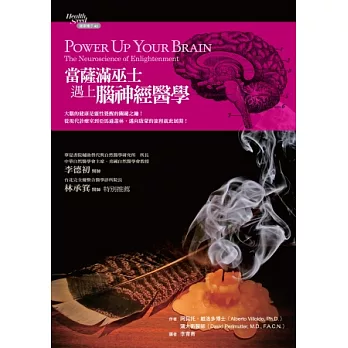(本文上接〈【排灣家庭遊祕魯】在印加高地上,巧遇通往過去與未來的迷幻植物(上)〉) 今天離開了奇幻的 Písac 小鎮,前往 Urubamba 集鎮;一路上原來順著 Urubamba 聖河蜿蜒而下,迫近聖城馬丘比丘,我們路程之順暢,沿途之愉快真是難以形容。
沒有隔閡的拉美鄉親
我們坐著當地的小車,跟大家擠,漸漸感覺與當地人之間好像沒有隔閡,我們還與上上下下的鄉親們玩自拍,他們似乎不太習慣,給他們看相片,還不好意思看,靦腆的程度像是霧一般,要有耐性等他散去。第一批坐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排小學年紀的學童,他們看到我們幾個亞洲罕面孔的時候,竟然沒有像 Písac 的鄉親那樣總是對我們笑,氣氛有些怪。 因為擠,我們倒是對於他們四、五個學童的五官與臉龐能夠仔細端詳或「面面相覷」:他們根本就是「鄒族臉」與「泰雅臉」,是屬台灣較高山區域的族群,讓我好奇他們的祖先在冰河時期越過北極的柏林海峽來到美洲而成為拉丁美洲裔之前,是否還跟南島民族有關係?這中間有很多理論,但我當下寧願相信他們根本是「台灣原住民」,因此我和莎莎(註 1)就輕鬆不客氣地認為他們是「鄉親」。 漸漸地,他們也放鬆起來,在小車廂內搞自拍,不亦樂乎。一路上,上下車的人們在我們面前交替,似乎是當地人一一派代表上來跟我們打招呼,有一位大媽還背著一個有英文字的書包上來,放在我正眼前,我不由得念起那幾句英文,因為我太喜歡了:他們根本就是「鄒族臉」與「泰雅臉」,好奇他們的祖先在冰河時期越過北極的柏林海峽來到美洲而成為拉丁美洲裔之前,是否跟南島民族有關係?
I don’t think it necessary for you to start tomorrow. I wish I could live together here.
(我想別再猶豫了,我應該住在這裡啦!)
這位大媽是怎樣,我念的時候顯然她不懂英文?但這訊息,好像郵差派來的 ── 對,沒錯,郵差只送信但不讀信,我只好回應她很多笑容,告訴她:「我們願意!」 哈!結果她與孫女就幫我們介紹起沿途的景點,雖然我們無法聽懂他們的西班牙文大概,但一旦我們聽到可以了解的關鍵字,也跟她呼應了起來,其實真懂與假懂之間,還很流暢。旅行是到達與離開的交織
看著沿路的 Urubamba 聖河,以及兩岸據說有 6 千公尺的高山,我們感覺這邁向聖城馬丘比丘的聖河,好像一條為我們鋪好的絲絨布道,讓我們飄然於途,邁向聖城,沿路陽光燦爛,遠山青綠之間,我們漸漸意識到,我們與 Písac 越來越遠。剛剛離開住了 5 天的夢幻小鎮,來到 Urubamba,我才發現我有點懂了 Písac 小鎮與 Ayahuasca(註 2)等致幻植物之種種。 「旅行」這件事很奇怪。其實「旅行」是動詞,就是一直動,由「到達」與「離開」相互交織著,讓我想到沿路常常看到的印加圖騰:蛇;他們畫的蛇,不讓人清楚知道頭尾,有時還綣成一圈好像咬著尾巴,這大概是一種循環的意向,蛇的波動蠕行,就是頭與尾之間的共振,「到達」與「離開」的象徵吧! 我們是 Urubamba 聖河裏悠遊的小蛇,勒!── 我們剛開始喜歡 Písac,就得離開,這就是旅行;當你要開始理解的時候,就要離開。真怪,我們來的目的不就是要理解嗎!懵懂之間就要離開。突然我發覺人類學與報導式文學的不同:人類學會想留下來不要離開,因為未知的太多,就會以為存在著尚未有能力完全認識的他者,想令人蹲下來,至於其他學問可能是「知道了」,就該走了。 但我發現,我們離開了,卻開始懂了。原來旅行也是一種學習方法。我們是 Urubamba 聖河裏悠遊的小蛇 ── 我們剛開始喜歡 Písac,就得離開,這就是旅行;當你要開始理解的時候,就要離開。

夢幻飛地之城 Písac
一路上看到真實的當地人,我漸漸可以想像當地人的臉孔後面的故事:在 Písac 小鎮,幾乎都是外國人之歐美人士,因此我可以看到法國男與台灣女,還有眾委內瑞拉美女等;在夢幻般的客棧裏,有著英國腔的女主人及安第斯原住民「服侍」著你,而牆上與路上到處都是服幻藥、參禪、打坐、修煉的傳單與外國人士 ── 可是這個「產業」幾乎都與當地人無關。 顯然這個 Písac 城是個「飛地」(註 3),如果不告訴你經緯度,你會以為在歐美的某個小鎮:夢幻飛地之城 Písac(我們心中給它的命名與地位)。 因此這裡可以有所謂師事亞馬孫叢林薩滿的法國籍巫師候選人,這裡的喝藥致幻儀式每週兩場,儘管所費不貲,幾乎場場爆滿,有人說有些場合幾乎百人以上。我問了一個住在 Písac 此地已經 4 年半的美國人的觀點,他講著 CNN 似的英文說,這裡的喝藥儀式已經商業化了,一兩個導師怎麼服務一百個人?還要「全方位」(holistic)地照顧每一個人的身心靈! 我們有了一個共同結論:儘管通往 Ayahuasca 之路偶爾神聖,卻往往非常商業。
The road to ayahuasca is sometimes holy but very often very commercial. (儘管通往 Ayahuasca 之路偶爾神聖,卻往往非常商業)
一旦商業化,神聖的真實面貌就越來越難辨了,我再一次延用剛才的比喻:神聖的程度像是霧一般,要有耐性等他散去。 哈!感謝我桌旁這兩位戰後嬰兒潮世代出生,曾深度嬉皮的「湯姆」與「哈克」以睿智的眼光與語氣跟我討論了這些,我竟然看到他倆小時候,小小無猜的頑童歷險記。 我們聊完,一起看著來這裡的許多外國年青人,有追尋的面孔,有虛無頹廢的面孔,有天真無邪的面孔。而這位住了 4 年半的美國大叔湯姆,他說他 4 年前有試過幾次 Ayahuasca,他的結論是:「你是真的,就會遇到真的,你是假的,就會遇到假的。」我問他身邊來探訪他的美國朋友哈克有沒有試過,他說,「我曾經試過『所有』,但我依然是鑽井工人」,他看看他身邊這位已經來此 4 年多的朋友哈克,兩個人一起給我一個眼神,充滿歷盡滄桑的睿智似乎告訴我,「過去現在未來都需要,但是當下最重要」,於是他們很一直地跟我談中國人的「當下」觀。 我臭蓋之間,發覺,迷幻的程度,只是要知道你能多清醒。 至於法國薩滿候選人,他說他在等 Ayahuasca 來告訴他,與他「合一」,這樣他就可以成為「正式」的薩滿來服務人群了,但他已等了 2 年多囉!我鼓勵並要求他說,當你成為之時,請告知我,我想成為你的學生。 我們以歐式的頰吻告別,我想我們已是朋友,希望這些兒緣分能再續。關於致幻植物之種種,剛好好友 Petra Wu 修女在 Facebook 引述一句話,抄來作為我的代結論:「若你不是已經找到祂,你便不會去找祂。」(Pascal)
(本文經原作者羅永清先生授權轉載,內容為暫時文稿,文字與圖片非經允許不得引用或轉載。)
編按
- 莎莎:作者的妻子,族名 Saiviq Kisasa,現為《臺灣原住民族國際訊息平台(IPTIP)》總編輯。
- Ayahuasca:學名 Banisteriopsis caapi,是生長在秘魯北方亞馬遜叢林的一種致幻藤類植物。當地原住民稱 aya 為「靈魂」之意,而 huasca 則意味「藤」,有「纏繞、捆綁靈魂」之意,也有人說是「死去一些」之意,好像透過此死亡之藤,可以釋放身心靈該死的部分。見〈【排灣家庭遊祕魯】在印加高地上,巧遇通往過去與未來的迷幻植物(上)〉。
- 飛地:一種人文地理概念,意指在某個地理區劃境內有一塊隸屬於他地的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