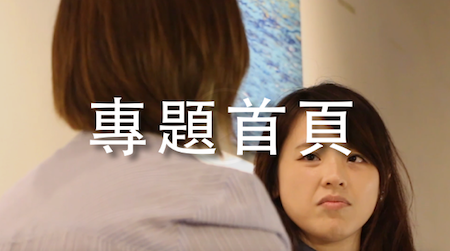與 18 歲的妳對話
「不可否認,這加分是有幫到我的,因為讓我有更好的管道可以到比較好的學習環境,在這方面我覺得我是受惠的。」Rimon 今年從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畢業,國中成績還不錯,能夠考上北一女;不過,她考量到為了減輕競爭壓力,選擇改去景美女中就讀,「一進去真的蠻痛苦的,每次都是死命追,卻沒有一次追成功,不管我再怎麼拼命都沒辦法像他們一樣厲害」。 她也笑說,除了國中與高中等放榜的兩個時間點最痛苦以外,其它時間點都很快樂。一些朋友會好意關心問她「想上哪間學校」、「加分後分數會變多少啊?」這類問題,幫忙計算分數建議可以考哪間,「好像被秤斤兩的一隻豬」,雖然 Rimon 知道他們是無心的,有時還是會覺得自己被傷到,因此盡量不主動提起對選擇學校的想法。 學生時代的「原住民議題」 現在有很多人質疑在大城市生活的原住民,不在原鄉的生活環境,是否加分優待政策的目的已日益模糊,不僅未必能明顯改善社經地位結構性弱勢的問題,還反而造成其它負面的聯想。泰雅族的 Rimon 從小在烏來長大,經常在部落裡看到小朋友,獨自在家沒有人照顧,父母都外出工作,阿嬤在種菜,「我看到還是有很多的需要,是這個政策存在的必要性」。 沛沛也曾問過身邊的原住民朋友加分政策對他的意義,她好奇如果不靠加分政策,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原住民族在教育劣勢的困境,但對於現存以種族為規範分類的質疑聲音,她也同意「 所有人在討論公不公平這一點,都忘記去看到底為什麼要讓它看起來稍微公平一點,就是因為當初『我先打斷你的腿』,所以我現在要還你東西。」 正如同當代的主流人群得以生活在一個無須察覺有「原住民族」存在的社會裡 —— 同時也理所當然地忽視了長期以來原住民族文化與語言流失的歷史。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0"] 正如同當代的主流人群得以生活在一個無須察覺有「原住民族」存在的社會裡 —— 同時也理所當然地忽視了長期以來原住民族文化與語言流失的歷史。圖攝於馬力巴部落,與本文所述人事物無關。(Credit: Yaway Suyun)[/caption]
小時候住基隆,在就近學校念書的沛沛自嘲念的是「放牛學校」,「隨便念都拿第一名」,曾經走在路上覺得自己像是孔雀一樣逍遙自在;但在高一時,無論怎麼念都只拿到班排 10 幾名、20 幾名,感到很氣餒,也同時茫然不清楚自己的興趣為何,未來可以做什麼工作。
對於原民升學可以加分最有感觸,是在國中升高中時,看到班上有一些原住民可能 3 年都在玩,升高中時卻可以輕輕鬆鬆填到更好的學校,「當時有一點吃味,可是我隱隱約約知道這樣做是為什麼,所以也是念頭一閃就讓它過去,沒有太多深究」。
「上高中以後,看到一些加分進來的原住民朋友,他們在課業上的努力要比人家多,那時候才有感覺到差別。不過因為我功課也很爛,應該比很多原住民都還要差很多喔,哈哈!」沛沛說,「加分政策對我而言沒有擠壓到我的空間,只是順水推舟了他們一把」。
事實上,現在各校針對原住民升學優待,是採外加名額方式錄取(通常佔原核定錄取人數2%),因此並不會影響到非原住民學生的名額與權益。
沛沛現在是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的學生,她想起在高中最好的朋友就是排灣族人,族名是Lavaus(拉法烏斯),「她的外表很『排灣』,眼睛很大,皮膚深色,一看就是原住民」。不過除了外表有明顯差異之外,她並不覺得原民身份對於相處有什麼其他影響,但會小心注意不要針對原民身份的刻板印象開玩笑,「她本人倒是滿不在意,覺得沒什麼,」沛沛笑說。
每當她問起有關原住民的事,Lavaus就會回說她不常住在部落,家裡也不說族語的,「可是他們家在排灣族是貴族階級,爸爸、叔叔都是警察,vuvu是女巫,但下面找不到人繼承,因為都信基督教了」。
Rimon也是基督徒,她說,或許是因為部落裡老人家對「共享」的理念,深刻影響她的待人處事,原本原住民的身份可能帶來很多令人絕望或負面的念頭,但信仰幫助她突破生命裡許多陷阱,希望要活出自己的面貌。
兩人的十年一覺電影夢
巧合的是,剛好都是因為《十年一覺電影夢》這本書,而燃起兩人對電影工作的熱情。「當然就是這本啊!」她們興奮地指著對方,沒想到一本書成為兩人最有共鳴的話題。
《十年一覺電影夢》是張靚蓓記錄李安十年電影生涯如何克服磨難的追夢歷程,李安兩次高考落榜、畢業後多年失業,做全職家庭煮夫,仍堅持心底的導演理想。當時的她們捧著這本書,心想「當導演好像還不錯」,不知道平行時空裡的另一個人,也做了同樣的志願決定。
那年,也是李安執導的電影《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熱映,轟動全台,印度男孩與孟加拉虎同船 200 餘天的故事,在電影藝術與商業技術上都備受討論。
少年 Pi 同時信仰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但在船上最無助的時候,似乎信仰什麼都沒有用,他於是向上天吶喊「為何要這樣對我」,這至今仍是沛沛印象最深刻的電影場景。Rimon 平時很喜歡觀察人的臉部,覺得中年以後的 Pi 那張講故事的臉,像是一張照片,所有劇情最終凝結在充滿回憶的臉部表情上。
對話至此,兩人彷彿交換了彼此在高中時期的記憶與心情,共通點是都曾有過升學的困擾,以及對於社會上不合理的現象感到質疑。
儘管自己的生活圈都很少有人關注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議題,但這幾年,確實有愈來愈多人在討論原民加分是否合理;Rimon 也同意臺灣作為多元族群的社會,族群之間能不能好好溝通是當務之急,也期望政府能更有願景與前瞻性。
「至少『會罵』就有機會去翻轉。」
延伸閱讀
正如同當代的主流人群得以生活在一個無須察覺有「原住民族」存在的社會裡 —— 同時也理所當然地忽視了長期以來原住民族文化與語言流失的歷史。圖攝於馬力巴部落,與本文所述人事物無關。(Credit: Yaway Suyun)[/caption]
小時候住基隆,在就近學校念書的沛沛自嘲念的是「放牛學校」,「隨便念都拿第一名」,曾經走在路上覺得自己像是孔雀一樣逍遙自在;但在高一時,無論怎麼念都只拿到班排 10 幾名、20 幾名,感到很氣餒,也同時茫然不清楚自己的興趣為何,未來可以做什麼工作。
對於原民升學可以加分最有感觸,是在國中升高中時,看到班上有一些原住民可能 3 年都在玩,升高中時卻可以輕輕鬆鬆填到更好的學校,「當時有一點吃味,可是我隱隱約約知道這樣做是為什麼,所以也是念頭一閃就讓它過去,沒有太多深究」。
「上高中以後,看到一些加分進來的原住民朋友,他們在課業上的努力要比人家多,那時候才有感覺到差別。不過因為我功課也很爛,應該比很多原住民都還要差很多喔,哈哈!」沛沛說,「加分政策對我而言沒有擠壓到我的空間,只是順水推舟了他們一把」。
事實上,現在各校針對原住民升學優待,是採外加名額方式錄取(通常佔原核定錄取人數2%),因此並不會影響到非原住民學生的名額與權益。
沛沛現在是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的學生,她想起在高中最好的朋友就是排灣族人,族名是Lavaus(拉法烏斯),「她的外表很『排灣』,眼睛很大,皮膚深色,一看就是原住民」。不過除了外表有明顯差異之外,她並不覺得原民身份對於相處有什麼其他影響,但會小心注意不要針對原民身份的刻板印象開玩笑,「她本人倒是滿不在意,覺得沒什麼,」沛沛笑說。
每當她問起有關原住民的事,Lavaus就會回說她不常住在部落,家裡也不說族語的,「可是他們家在排灣族是貴族階級,爸爸、叔叔都是警察,vuvu是女巫,但下面找不到人繼承,因為都信基督教了」。
Rimon也是基督徒,她說,或許是因為部落裡老人家對「共享」的理念,深刻影響她的待人處事,原本原住民的身份可能帶來很多令人絕望或負面的念頭,但信仰幫助她突破生命裡許多陷阱,希望要活出自己的面貌。
兩人的十年一覺電影夢
巧合的是,剛好都是因為《十年一覺電影夢》這本書,而燃起兩人對電影工作的熱情。「當然就是這本啊!」她們興奮地指著對方,沒想到一本書成為兩人最有共鳴的話題。
《十年一覺電影夢》是張靚蓓記錄李安十年電影生涯如何克服磨難的追夢歷程,李安兩次高考落榜、畢業後多年失業,做全職家庭煮夫,仍堅持心底的導演理想。當時的她們捧著這本書,心想「當導演好像還不錯」,不知道平行時空裡的另一個人,也做了同樣的志願決定。
那年,也是李安執導的電影《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熱映,轟動全台,印度男孩與孟加拉虎同船 200 餘天的故事,在電影藝術與商業技術上都備受討論。
少年 Pi 同時信仰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但在船上最無助的時候,似乎信仰什麼都沒有用,他於是向上天吶喊「為何要這樣對我」,這至今仍是沛沛印象最深刻的電影場景。Rimon 平時很喜歡觀察人的臉部,覺得中年以後的 Pi 那張講故事的臉,像是一張照片,所有劇情最終凝結在充滿回憶的臉部表情上。
對話至此,兩人彷彿交換了彼此在高中時期的記憶與心情,共通點是都曾有過升學的困擾,以及對於社會上不合理的現象感到質疑。
儘管自己的生活圈都很少有人關注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議題,但這幾年,確實有愈來愈多人在討論原民加分是否合理;Rimon 也同意臺灣作為多元族群的社會,族群之間能不能好好溝通是當務之急,也期望政府能更有願景與前瞻性。
「至少『會罵』就有機會去翻轉。」
延伸閱讀
- 原民生看考試加分:原住民學生考試加分政策,到底是「加分」還是「負分」?
- 「福利」背後的脈絡:國家考題背後的弔詭隱含:原民已經得到很多福利,為何還不滿足?
企劃:Mata Taiwan 文字:Vanessa 攝影、剪輯:曾金進、郭沛盈 受訪:Rimon、郭沛盈 場地協力:旬印咖啡